《心理咨询师的部落传说》是很多年前写的,当时我跟两位心理学编辑坐在车上,一位是徐维东老师,她是蛮有名的儿童游戏治疗师,精于沙盘治疗;另一位是郑燕老师,她编辑出版过很多心理学书,如《佛学与心理学对话译丛》。我们三人在谈到一些书的时候,我有一个想法突然冒了出来:与其写一本专业书,不如写一本大家都能读懂并且有一定内涵的书。
《心理咨询师的部落传说》的创作背景
当年参加中德班的时候,我的督导师马克是著名分析师海曼的学生,他给我们讲过海曼的故事,这个故事是我这本书成型的萌芽。
弗洛伊德最早提出了反移情的概念,他建议在精神分析中应该禁止反移情的出现。到了1950年前后,著名分析家海曼重新使用了这个概念。

海曼最早跟着克莱因学习,因为克莱因本人不是很好相处,两人合不来,于是她离开克莱因,跟随安娜·弗洛伊德。海曼在跟安娜工作期间,他们经常一起讨论学术,在讨论中他提出了一个自己的观点。他认为咨询中的很多东西都是咨询师的自我反应,这个自我反应就是反移情,反移情是一种自然性,并且有助于咨询,所以作为精神分析师不能太装。
有一次,海曼跟另一位分析师在法兰克福的讲座上展开讨论的时候,马克坐在下面听到海曼说:如果有人送她一束花,她会很高兴;如果有来访者送她一束花,她也会欣然接受,但是接受之后,她会思考并询问来访者“如果我没有接受这束花,会给你带来什么”,用这种方式进行探索。海曼给出一个结论:咨询师如果隐蔽在咨询角色之外,很不真实地躲避一些东西,这样的咨询就会没有生命。当然,这个观点存在争议。
目前,精神分析的波士顿小组在《心理治疗的改变》里有一些临床经验说明。研究认为,当咨询师和来访者能够“赤裸相见”的时候,大家都能够放下彼此的防御和身份,在这种真实关系中构建一个相遇时刻,这个相遇时刻在精神分析中具有生命力和转化力,在这个过程中,一个人的心在这个位置上就打开了。这个观点给了我很大的启发:在临床咨询中,我们究竟跟来访者是什么关系?这是个很有意义的问题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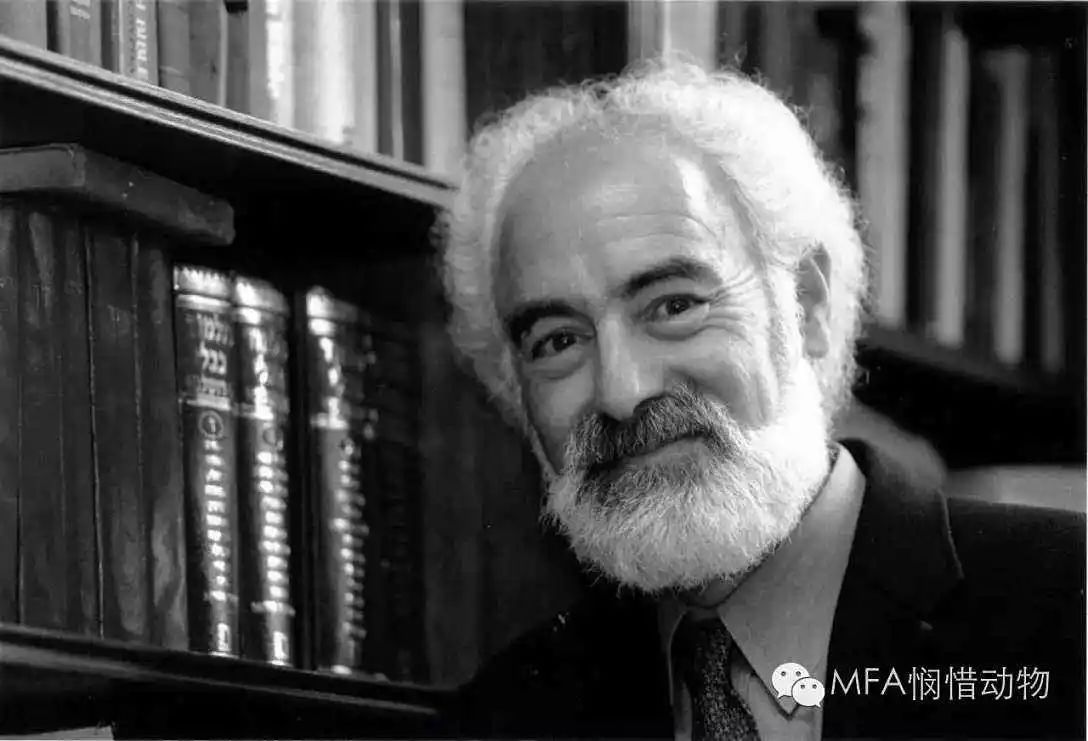
马丁·布伯是著名的存在主义哲学家,早年在德国和比利时的精神病院学习过,有精神医学的受训背景,曾经跟卡尔·罗杰斯、皮尔斯(格式塔疗法创始人)有过对话。他的观点是:真正的精神分析师与其病人的关系,同样充分表明了相互性的标准局限性。如果咨询师只是满足于“分析”病人,即从心理世界中挖掘出无意识的要素,并把通过这种程序加以转变了的心理投射到有意识的人生工作中去,也许他的治疗会取得一定的成功,在最好的情况下,他能帮助心理紊乱无序的人在某种程度上调整自己、整合自己,但是,他却无法完成真正的任务——让萎缩的人格中心获得整合。
唯有这样的医生方能胜任此任务:以深邃的眼光洞见到病患心灵中潜伏的统一性。但若欲如此,医生必须与病人建立人格和人格间的伙伴关系,且不能把他当做观察、研究的对象。为了把这种统一性释放出来,为了让病人与世界建立新的和谐并实现其统一性,他的一生必须像老师一样,不能拘泥于两极关系中自己的一方面,应同时凭借“现实性”的力量站到另一极去,设身处地地体会治疗效果。同样,倘若病人自己逆行“总结”,站在医生的一极来体验效果,则这样特定的“治疗”关系便不复存在。在人际关系中,既若亲兄弟,又落落寡合,唯此种人才可治疗他人、教育他人。如果在一种关系里,其中的一方要有目的、有计划地对另一方实施影响,则这种关系里“我—你”的态度所依据的乃是一种不完整的存在、一种注定不可能完善的相互性。
我在中德班听马克博士讲他跟海曼的关系的时候,就想到了上面这段话。我对这段话非常有感觉,而且这段话里呈现了一个故事。这个故事并不是中德班教学大纲中规定必须要讲的东西,但往往是这些“不必要”传递出一些内容,这些内容对理解海曼的自然性有很大帮助。可见,故事的传递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某些人、某些理论以及更好的咨询是什么。

这些故事在展现的时候,就像言传身教里的身教,身教的感觉就像新鲜出炉的面包,充满了生命力。这些故事引发了我对历史的不同看法。我们国家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,从《史记》开始,每个朝代的历史都被记录和言说。以前我在读历史的时候,往往需要读很多遍,例如公元657年,考试的时候会问这个年代发生了什么事情,于是我们就去背诵历史课本中的事件,好顺利通过考试。但是,历史的意义仅限于此吗?
即使我知道了公元657年有哪些历史事件,也对这段历史毫无感觉。公元657年发生了很多事,比如唐朝和回鹘发生战争,玄奘和唐高宗去西明寺开光等。历史只记录了大事件,却没有记录民间故事,比如,玄奘陪唐高宗回来的路上发生了什么?又如,王玄策代表大唐出使印度,被印度虏获,逃出后带领尼泊尔和吐藩军队攻回印度俘虏了印度王,使大唐在中亚和南亚重新建立了威望等,这些细节在历史上很少被记载。如果历史只是为了记录,那么它的意义就只限于被言说。
我们在看一件事情的时候,不能只看到它的表面。同样,当我们看心理学史、精神分析发展史、认知治疗发展史和人本主义发展史的时候,不能只看到单向的口述的历史事件。人类学研究发现,一个部落和一种文化的精神,往往都是通过故事传递下来的,因为那个年代所用的工具、技术和其他东西并不那么坚固。一个历史时代会被淘汰,但是古来的故事和它赋予我们的精神却会流传甚久,就像中国人说起皇帝、轩辕、神农、尧、舜、禹、汤和孔子的故事一样。虽然这些故事离我们很遥远,也有过很多变形,但它的根源和结构并没有失去,它传递给我们的是一种中国人的做事方式,这种精神力量一直存在。

精神分析、认知治疗、人本主义、家庭治疗等,每个学科都有自己很重要的故事,这些故事以口传的形式传递,就像禅宗的教外别传一样,反映出很多很重要的东西,很有意义。我们在传递故事的时候,都有自己对故事的偏见在里面,这个偏见是我们诠释的观点,偏见是普遍的,因为每个人都来自不同的地方、不同的父母、不同的姓氏,姓氏代表我们每个人都不同的故事。例如,我姓徐,徐姓可能跟徐偃王的故事有关:当时周天子西行,整个国家发生动荡,徐偃王在徐州集结军队想重新拥立天子,于是周天子急忙赶回。当天晚上,徐偃王想到第二日两军对垒必定死伤无数,既然周天子已经回来,如果他能够管理好国家,就不需要这场战争了,于是解散军队隐居起来。但对这个故事是有不少解释版本的。

弗洛伊德的故事
作为心理咨询师,我们必然会说起弗洛伊德的故事。今年是弗洛伊德去世83周年,我们不禁会想知道,弗洛伊德是如何去世的呢?弗洛伊德患有口腔癌,他跟医生约定,如果到了实在无法治疗的时候,就给他使用吗啡。两三支剂量的吗啡可以致死,也就是说,弗洛伊德采用安乐死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弗洛伊德面对死亡如此坦然,足以看到他是作为一个人的存在,而不是作为书中人物的存在。
弗洛伊德还有很多故事,比如治疗他的病人狼人的故事。在弗洛伊德去世很多年后,一位人类学家对狼人进行了采访,发现狼人说他自己并没有被弗洛伊德治愈,这引起了精神分析协会的紧张,毕竟弗洛伊德曾表示狼人的案例比较成功。
直到狼人去世后,他的档案才被公布于众。狼人患有精神病结构的抑郁,在尝试了所有治疗都没有效果后,他找到了弗洛伊德。狼人是非常富有的贵族,所以能够接受长期的精神分析。分析的开始两年,狼人的症状有所缓解,但是因为弗洛伊德那时病情严重,做了30多次手术后,嘴巴的上颚全部切除,两个鼻窦直接展开,嘴里还有臭气,需要接受治疗和休息,于是将狼人转介给他的两个学生。一段时间后,由于两个学生的治疗都不太成功,于是弗洛伊德又将狼人转回到自己这里做治疗,几年后,弗洛伊德单方面宣布结束治疗。
狼人曾回忆说,他与弗洛伊德有链接,在治疗中他感受到的并不是弗洛伊德的诠释,而是自体客体经验,即弗洛伊德在某种程度上与狼人有所共鸣的经验。弗洛伊德还曾邀请狼人与他的家人共同就餐,他感觉弗洛伊德是一位温暖的老人,总是眼巴巴地希望他能够说出一些潜意识里的东西,但他最后还是让这位老人失望了,因为他并不知道弗洛伊德让他说些什么。
虽然这个个案并没有彻底痊愈,但从以上的描述来看,治疗还是有一定的成功的,因为狼人的症状改善了,而且对狼人来说,这是一段印象深刻且非常重要的经历。
弗洛伊德的两位学生却不同,狼人回忆,这两位分析家很节制,节制到不太说话,这让狼人感觉很不好。从当代精神分析的治疗观点我们知道,如果分析师对于具有精神病结构的来访者过于节制的话,来访者就会投射出很多妄想,咨询师的沉默会让来访者HOLD不住自己的妄想,所以不利于治疗。
弗洛伊德曾有过一次强烈的反移情,来访者是位高级学者,在埃及做了几十年的考古工作。在做治疗的时候,弗洛伊德满脑子都是关于埃及的联想,这让他很兴奋,因为他喜欢搜集古董。所以在治疗过程中,他经常打断来访者询问埃及的事情,几个月后,他把这位来访者转介了,因为如此强烈的反移情对来访者是有害的。
弗洛伊德是个工作狂。按照犹太人的习惯,他每天早上六点起床,吃早餐,七点多开始给人做分析,一直工作到下午,吃个点心,休息一刻钟,然后继续工作到晚上八九点,十点吃晚餐,饭后出去散步半个小时到一小时,回来后看文献、写东西,一直到十一二点睡觉。虽然工作量很大,但他很享受。
除了工作,弗洛伊德经常去意大利休假,休假的时候不接受分析;他喜欢收集各国的文物和古董,在他伦敦和维也纳的房子里,我们能看到他搜集的很多古董,这还不是全部,因为他从奥地利逃离的时候,其中很多都被纳粹没收了;他还是一位业余人类学家,著有《图腾与禁忌》和《摩西与一神教》,这两本书是古典人类学的经典作品,经常被讨论。

奥托·兰克是弗洛伊德的养子。兰克小时候很穷,没办法负担学费,阿德勒遇到兰克的时候,跟他说起精神分析,兰克听后很感兴趣,于是买了弗洛伊德的书来读,并写了一篇艺术跟精神分析相关的文章拿给阿德勒看。阿德勒看后很惊讶,这个十六七岁的孩子居然能写出这样的文章,于是把文章拿给弗洛伊德,弗洛伊德看过文章后约见了兰克。二人见面后,弗洛伊德决定资助兰克去上学,后来兰克成为非常有成就的精神分析师,晚年去了美国。
弗洛伊德的故事还有很多,这些故事不排除被加工过的可能,但这些口传的生动的历史更具有生命力,能让我们更加理解弗洛伊德的理论,让弗洛伊德的理论立体地“活着”展现在人们面前。这些历史不是言传,而是很直接的身教。这些启发性的故事,让我们看到整个分析的进程里充满了生命力,这些生命力就是我创作《心理咨询师的部落传说》的初衷。
如何成为好的咨询师?
会吃喝玩乐才是好的分析家。这句话虽然说起来有点夸张,但一个人学习心理咨询,不能整天只知道看书和做咨询,过度沉浸在理论和流派中,而是要有自己的生活和爱好,要跟亲戚、家人、朋友保持一定的关系,这是作为人很重要的东西。
我曾经的督导师现在已经快80岁了,仍然经常去听歌剧、看话剧和电影。就像马丁·布伯说的,分析师要跟自己的生活相联接,因为治疗中的很多东西都是从生活和其他体验中得来的,比如话剧、戏剧、电影、历史著作等。
我们要丰富自己的人生体验,与来访者有类似的经验,这样才能真正理解来访者。比如,人本取向的咨询师在倾听的时候,就像进入了对方的精神世界,在来访者的世界里去体验他如何看待这个世界。当我们能够这样去理解的时候,分析才有利。在这个过程中,来访者也会在体验中体会自己,咨询师能够理解来访者的治疗效果,来访者也站在咨询师的角度看自己,这是双元的主体间过程。
很多同道都知道,我到各个地方的时候都会晒一些美食的照片,这是件很有乐趣的事情。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习俗,比如贵阳人喜欢吃虫子,国内其他地方的人,会认为吃虫子很恐怖,从心理治疗的标准来说吃虫子是饮食障碍——异食癖,但从人类学角度来看,异食癖是人类设定的,因为习俗不同,我们恐惧这种行为、不理解这种行为,所以把这定义为异食癖,其实这只是一种饮食方法而已。
由此可见,我们在理解来访者的时候,即使我们没有直接经验,也可以通过间接经验让我们的偏见变得少一点;即使偏见变少了,我们还是要保持一些偏见,因为一个人承认自己有偏见并不可耻,一个人说自己没有偏见和立场才最让人讨厌。
我们跟朋友出去吃饭的时候,会问对方想吃什么,如果对方回答随便,我们会认为随便意味着没有偏见,结果你点了菜以后,对方并不一定会满意,甚至百般挑剔。我们都试图让自己变得没有偏见,但事实是,我们都不是随便的人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和独特的成长史,都有自己的建构和生命历程,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。诠释学观点认为,每个人的生活都是历史丰富的,历史丰富性就是让一个人对世界带着足够的偏见,这种偏见会成为这个人所谓的个性和世界观。当我们承认偏见的时候,对世界的偏见就会少一点。
例如我是认知行为取向的治疗师,但是我今天讲了很多精神分析的故事,这就是偏见;也有一些人把弗洛伊德和荣格比较,相比弗洛伊德,荣格很富有,因为他的妻子是万国集团的继承人,这也是偏见。当我们带着偏见去评判的时候,会看到一些冲突;我们每个人都有冲突,在弗洛伊德看来,一个健康的人也有神经症冲突,所以冲突本身并不可怕。
当我们发现历史和生活中的偏见时,偏见所形成的世界和体验,反而让我们具有了反身性的意识,因此让我们跟动物区分开来。以前的历史认为是劳动和工具创造了人类,现在的动物行为学研究发现,水獭、猴子、猩猩等动物也会使用工具,会使用工具并不能区分动物和人类,人类和动物最大的区别就是反身性的意识。人类有历史,而动物没有。
我们在叙述故事的时候,故事也反身到我们自身的体验上,我们并不是体验故事中的那个人,而是那个人让我们自身产生了某种体验,并整合为我们对世界新的进展。刚刚我们说到了异食癖,第一次到了贵阳以后,我像异食癖患者一样去吃虫子,并开玩笑说,以后要在贵阳建立一条原则,到贵阳讲课的老师一定要吃虫子,由此看看我们对这个问题修通得如何。其实我想说明的是,我们要跨域自己,去看一些东西。当然,这个世界很广大,我们无法跨越所有的东西,比如我不可能去尝试吸毒,这是人类的有限性,人类会有偏见、有好恶、有选择,所以我们成为了凡人。不过,在这个位置上,作为咨询师,我们可以把路走得更远一些。

还有很多故事,比如荣格,大家都知道《危险关系》这部电影,讲的是荣格跟他的来访者萨宾娜发生了性行为,虽然荣格在其他方面做得很好,但他是一个情感渣男,除了萨宾娜外,荣格还跟另外一个学生发生了性行为。跟他的妻子艾玛·荣格摊牌以后,艾玛只能同意和接受他有婚外情的事实。我们看荣格故事的时候,要跟他的理论区分来看,毕竟没有谁可以很完美。
卡尔·罗杰斯中年的时候给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做治疗,他在理解来访者后慢慢向这个人认同了,因为对方是精神分裂症患者,罗杰斯开始产生了幻视和幻听,变得很警惕。经过督导以后,他发现自己没办法治疗这个病人,于是单方面离开了来访者,这对来访者来说等于被抛弃。罗杰斯因此接到了伦理举报,经过很长一段时间,才慢慢恢复了一点。

欧文·亚龙的师傅罗洛·梅晚年时经历了离婚,生活比较糟糕,因为当时很有名,不好意思找别人做治疗,于是找到了欧文·亚龙做分析。欧文·亚龙曾在罗洛·梅那里分析过,所以这并不符合伦理,虽然欧文·亚龙自己没有说,但这件事情却真实存在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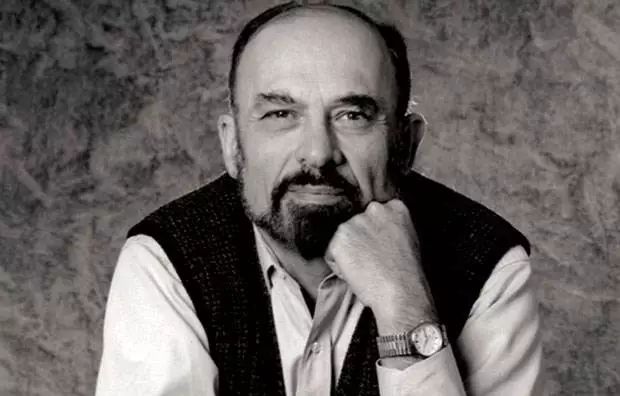
大家可以看到,无论是著名的咨询师还是我们,都是十分有限的人类。当我们能够识破这一点,就会发现:我们做咨询的时候,要像一个人一样跟来访者工作,这样就不会陷入自大的立场——开放的、凡人的、非自大的立场对我们做心理咨询很有帮助。
在《心理咨询师的部落传说》这本书中,记录了一个个有生命的故事,这些故事鲜活地展现在我们眼前,而不是作为历史被言传。
《史记》并不只是官方的历史,而是历史上杰出的典范,书中每一段后面都有“司马公曰”,这些“曰”是司马迁对历史事件的意见,这是带有生命的个性化正史。
我最近在写另外一本书,这本书可以说是另外一本《史记》。中国心理咨询正在进入从无到有突飞猛进发展的阶段,每个人都在用生命展示自己的故事,每个故事都有很多面向,我想让自己像一个史官一样,把这些故事和人物记录下来。这个史官是自由的,没有任何牵制的,若干年后,这些故事可以成为有生命的东西在这个轮回的世界里递传。
声明:本站内容与配图转载于网络,我们不做任何商业用途,由于部分内容无法与权利人取得联系,稿费领取与侵权删除请联系我们,联系方式请点击【侵权与稿费】。
求助问答
最新测试
207194 人想测
立即测试
224814 人想测
立即测试
204025 人想测
立即测试
185278 人想测
立即测试
181517 人想测
立即测试